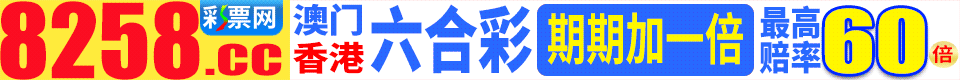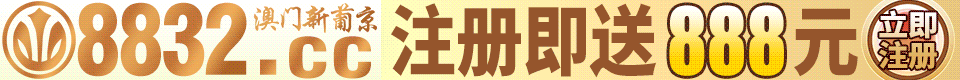巫山蓝
第一回洞房中初识风月
诗曰:
刘郎慢道入天台,处处档花绕洞栽。
贾午高香可窃,巫山云雨偏梦来。
诗因写意凭衷诉,户为寻欢待目开。
多少风流说不尽,偶编新语莫疑猜。
话说明朝弘治年间,松江府华亭县八团内沙地方,有一花姓人家,家主名唤花成春,娶妻保氏,皆三十有馀,因常做药材生意,故家道殷实,生得一男一女,男的唤花聪,年已十八,女名玉月,年已十六,兄妹二人一般模样,俱生得身躯袅娜,态度娉婷,可谓金童玉女。
花成春夫妇生得这对儿女,十分欢喜,花聪十岁时,上学攻书,可甚不聪明,苦了先生。费尽许多力气,读了三年,书史一句不曾记得。竟同了几个学生,朝夕顽耍。父亲虽严,哪里曾骇过;先生虽教,哪里肯听。
他父亲见他不似成器的样儿了,便思付恁般顽子,不能成器,倒不如歇了学,待他长成时,与他些本钱,做些生意也罢。故送了先生些束修,竟不读书了。
及至后来,越发拘束不定,夫妻商议,道:「孩儿不肖,年已长成。终日闲游,不能转头,不若娶一房媳妇与他,或许留得住。那时劝他务些生业,也未可知。」
成春道:「我心正欲如此,事不宜迟。」即时就去寻了媒婆。那媒婆肚里都有帐单的,却说道:「几家女子,某家某家可好幺?」
成春听了道:「这几家倒也使得,但不知何人是姻缘,须当对神卜问,吉者便成。」遂别了媒婆,竟投卜肆。占得徐家女子倒是姻缘。馀非吉兆,思忖道:「也罢,用了徐家。」遂又去见了媒婆,央他去说。
原来此女名唤琼英,幼年父母双亡,并无亲族。倒在姑妈家里养成,姑夫又死了,人嫌他无娘教训的女儿,故此十六岁尚未有人来定。这日,恰好媒婆去说,这徐氏姑娘又与他相隔不远,原晓得花家事,日子好过,但不知儿子近日何如。自古媒人口,无量斗,未免赞助些好话来,那徐氏信了,即时出了八字让花家择日成亲,少不得备成六礼,迎娶过门,请集诸亲,拜堂合卺。揭起方巾花扇,诸人俱看新人生得如何。但见:
秋水盈盈两眼,春山淡淡双娥。金莲小巧袜凌波,嫩脸风弹待被。唇似樱桃红锭,乌丝巧挽云螺。皆疑月殿坠嫦娥,少天香玉兔。
诸人一见,果是美貌,无不十分称好。一夜花烛酒筵,天明方散。末免三朝满月,整治酒席,这且不题。
这夜,待宾客散尽,花聪手挽琼英,并至洞房,将琼英抱起,置于榻上,正欲解琼英腰带,琼英凤眼乜斜,睨了花聪一眼,笑道:「干甚如此急,你岂不知『心急吃不了热豆腐幺』?」一头说一头勾住花聪颈儿,将口儿凑将上来,吐出丁香舌儿,抵入花聪口中,大吮大咂。
俄尔,琼英浑身酥痒,娇喘微微,遂腾出手来,慢慢解那花聪衣绊,摩抚片时,旋即脱去自家上衣,露出那嫩白的胸脯,两只酥乳儿玲珑挺拔,花聪看得情兴飞扬,遂急抽出双手,自琼英小腹徐徐上移,到得胸上,急握住那对玉乳儿,轻抚轻摩,嘻笑道:「心肝生得好乳儿,与我吃吃!」一头说一头含住奶头,咂将起来,少顷,又捏住那乳饼儿,道:「心肝,恁般好东西无人耍过罢?」
琼英凤眼眨了眨,道:「有人耍过,不但耍过,而且吃过哩!」花聪见他一本正经,不觉信以为真,遂拿开手,责问琼英道:「是何许人也?你得从实招来!”
琼英接话道:「心肝怎的如此火大,方才不是有人又是耍,又是吮咂不止幺?」花聪这才恍然大悟,见琼英戏言,遂笑道:「你也哄我,看我怎的治罪于你!」一头说一头将双手搔琼英腋下,惹得琼英笑个不住。
稍停,琼英即解了自家腰带,花聪顺势脱他裤儿,琼英将臀抬起,三下两下脱了个精赤条条。虽为夫妻,琼英毕竟是初经人事,未免有些羞怯,急用双手将那话儿遮住,缩做一团,花聪见他如此娇态,淫兴登起,腰间那物儿挺得极高,将个裤儿顶起,犹如斗签般,遂褪去裤儿,偎于琼英身后,将那铁杵般阳物对着那妙物儿,直戳个不停。
琼英觉那物儿如火炭般热烙,登时情兴勃发,周身酥软,即转身过来,抱过花聪,吐过丁香舌儿,亲了一回,口中哼哼不住。花聪知他兴起,遂探手于琼英胯间,轻抚那丰隆柔润的话儿,并不觉一根毛儿,唯觉那物儿高堆堆,紧揪揪,中间一道肉缝儿,犹初发酵的馒头。再探一指进入,那肉洞儿窄小温热,爽快无比,往来数回,琼英体酥肉麻,□内气喘,香汗如珠,叫快不绝。
花聪知其春欲钻心,遂翻身而起,扛起金莲,架于肩上,扶住紫昂昂阳物,照准鲜红肉洞儿刺去。琼英初次开苞,紧张有馀,花聪往里入那当儿,他早将臀儿一闪,小和尚扑了个空,小和尚怒发冲冠,胀得通体发紫。花聪道:「我的乖肉儿,别怕,不痛人的!」
琼英俏脸蛋儿赤红,羞答答的点头道:「心肝,你且慢些入,我那话儿窄窄的,岂能容下你那大家伙!」言毕,花聪再行刺入,却进寸许,又往里一耸,又进些许,琼英觉阴户如刀刺般疼痛,胀得难过,遂哀叫道:「亲哥哥,我那小穴儿痛,待我歇会儿。」花聪那听,末等他话完,又猛的一顶,听叱的一声,又进了半截,琼英叫痛,急用手推住,额头汗珠渗出,口内嗳呀声不断。
花聪见他痛苦模样,怜其娇躯,遂长出口气儿,停了下来,探手去轻抚琼英那嫩穴儿,亦不多时,花聪将琼英手移开,双手扳住琼英肥臀,腰一发力,一耸再一顶,那物儿方才全根进入,琼英觉疼痛不已,又探手握住阳物根底,止住不动。
稍歇片时,花聪轻抽缓送,行那九浅一深之法儿,琼英阴内骚痒,两只脚儿紧夹,口内伊呀乱叫,花聪知他佳境欲至,遂加紧抽送,刹时千馀开外,的琼英星眸紧闭,体颤头摇,下面唧唧抽扯之声不绝,浪水儿流了一席,含着数点猩红,已狼藉一片。
战罢两个时辰,琼英觉腰酸腿痛,周身瘫软,花聪亦气力不支,遂放下金莲,覆于琼英肚腹之上,贾其馀力,狠命的捣弄。琼英支起手臂,双手托住玉臀,将情穴高凹,拼命迎凑。
二人合做一处,口儿互抵香津,花聪气喘嘘嘘道:「心肝,的你爽快幺?」
琼英笑道:「我的心肝乖肉儿,你真个会人,可爽利死我了!自娘肚里钻出,从末得知如此快活,不想男人生得那妙物,竟令女人这般爽利!」
花聪道:「我亦如此!」话说到兴浓处,淫兴又动,花聪扶住阳物,再行刺入,趁着些淫水儿,不多用力,便一溜而入,直抵花心,遂紧靠那处,往里揉摩,美不可言,惹得琼英花心发痒,熬禁不住,急探手抱住花聪臀儿,道:「心肝,我那花心痒极,你且速些抽送!」
花聪闻罢,掀腾不住,紧缓异常,弄得自家如坠云雾里一般,快活难当,遂紧抽紧送,约有二千馀度,琼英兴发如狂,柳腰款摆,连连叫爽,一颠一耸,迎合花聪,叱叱床摇之声,唧唧抽插之声,响成一片。
干了一个时辰,琼英被覆得胸闷气喘,遂翻身扒起,跪于床上,将个丰肥白嫩的臀儿耸起,回眸睨了花聪一眼,花聪会其意,急扒起跪于琼英臀后,将两股一分,那细细嫩嫩光光油油的妙物尽收眼底,似鸡冠微吐,如桃红两瓣,遂捻住阳物,照准那缝儿正中,着力刺去,听嗳唷一声,不知怎的,且看下回分解。
第二回后园赏花行云雨
诗曰:
俊男靓女两相宜,从天分下好佳期。
拨雨撩云莫乐事,吟月咏风是良媒。
襄王已悟阳台梦,巫女亦识鱼水欢。
锦帐一宵春意满,高唐暮暮与朝朝。
话说花聪搂住琼英玉臀,猛的,往里一耸,琼英身儿往前移了半尺,不想头抵床栏,撞破了头皮,登时鼓起个血包儿,麻麻的痛,亦不顾及,阴内骚痒难禁,犹千百只蚁子钻扒,遂手撑床栏,令花聪立马大.
花聪淫兴正浓,遂周身摇动,将那阳物狂抽猛耸,左冲右撞。琼英被那滚热的物儿刺得美快无比,口中叫道:「亲肉达达,尽情弄罢,真个爽利死我了!」
花聪加力抽耸,威风不减,琼英情穴相迎,不甘示弱,提捣二千馀度,琼英昏昏而眠,不复于人间矣。花聪见状,仍不罢手,又狠刺多时,琼英又被醒转来,道:「心肝亲亲肉儿,你可真个神勇,险些将我死了!我遇你这般男人,亦不枉来世一遭!」
花聪道:「我的亲亲心肝,自此之后,你我可日夜欢乐,尽享人间至乐!」一头说一头狠送狂抽,琼英兴恣情浓,亦前冲后顿,不住迎承花聪,又战有千馀回,花聪觉腰下一软,不觉洋洋大矣。
琼英正至佳境,经这阳精一淋,花心更是酥痒畅快,遂转身将花聪推仰于床,覆于花聪胯上,握住阳物,低头把那樱口一启,大肆吮咂起来,舌绕龟棱,唇贴青筋,又将手掳扬数十回,花聪淫兴大起,将身一挺,那物儿又硬梆梆的,遂纵身下床,立于床前,掇起金莲儿,照准那千人爱万人欢的情穴,将阳物一挺而入,耸身大弄起来。
琼英畅快,耸动不住,情穴相迎。花聪见他骚淫太甚,竟大展平生本事,狂抽乱插,刹时二千馀下,的琼英魂飞天外,魄散九霄,气喘急急,若身在浮云,双眸紧闭,口内淫言俏语,心肝达达,亲肉乖乖,叫个不断,好不快活。
经这一番大弄,琼英被翻桃浪,牝内波涛汹涌,丢之数次,昏迷二三遭,花聪遂将身俯下,紧贴酥胸。琼英亦勾住花聪颈儿,将三寸丁香舌儿吐出,花聪把口接住,你来我往,下面亦耸个不停。阳物于牝内大肆出入,点点如禽啄食,下下似蛇吐信。琼英周身难耐,被射得钗堕鬃乱,美得身颤腰酥。
花聪愈战愈勇,怎奈琼英紧勾颈儿,两身又紧紧相贴,不便发力,遂捞起琼英,双手托其玉臀,一抬一放,于屋内走马观花般的弄。琼英觉着有趣,两腿倒控花聪腰间,双肘置于花聪肩上,乘势一起一落,煞是得趣。
又弄有半个时辰,花聪直呼累极,再无力托起琼英身儿,遂道:「小亲亲,依旧床上做耍,如此忒累!」一头说一头将琼英置回床上,自家上了床榻,仰面而睡,气喘如牛,胯间那物儿依旧直挺挺的,昂昂然冲天而立。
琼英见状,忙把住摇了几摇,道:「郎君生得如此浪东西,恁般长大,奇哉!奇哉!速将衣盖好,不可冻坏了他。」话虽如此,岂肯就此罢手,不管三七廿一,又一阵大掳大扬,阳物似比前粗硬许多,遂腾身而起,蹲身胯间,捻住阳物,以牝就之,置于牝门,猛的坐将下去,听叱的一声,已进大半截,研研擦擦,方全根进入,花房窄小,阳物粗大,故间不容发,满满实实。
琼英十分美快,一起一落,套了一阵,花聪于下,不住颠耸,约有半个时辰,弄的淫水泛溢不堪,缘阳物流下,琼英淫声浪语,手扪双乳,快活至极。
花聪不想片时,淫兴又起,遂翻身扒起,将琼英覆于身下,照准白生生的牝户,着力刺去,急急抽送八百馀回,因琼英骚得极至,故又花心紧张丢了身子,花聪亦腰酥背软,双脚腾空,身子一挺,了。二人绸缪多时,时值五更鼓响,方才交股贴肉,搂抱而眠。
自此夫妇二人如胶投漆,如鱼得水,甚是和睦。一日,正值隆冬天气,后园梅花正发,香气袭人。花聪闻之,喜不自生,便对琼英道:「心肝,后园梅花香秀,香气爱人,极宜赏玩,不可错过花期。」琼英闻罢,欣然而应,遂与花聪并至后园,见红白相间,清香扑鼻,遂摆酒看于梅花树下,二人你一杯我一盏,对饮开来。酒过数巡,皆有五六分醉意,乘着酒兴,花聪将琼英搂于怀中,一头亲嘴咂舌,一头轻解衣绊,两手不住游衍于酥胸,扪住那对玉乳儿,摩抚揉弄不止,琼英亦娇喘,一副骚淫模样。
少顷,琼英将手探入花聪胯间,隔着裤儿轻捻那物儿,不想那物儿早竖将起来,跃跃欲试,遂急解了裤儿,将阳物从洞中掏出,自家又急褪了裤儿,露出那紧扎扎的牝户,花聪知他兴至,遂将琼英背靠梅树,将两股一掰,欲行刺入,琼英着力帮衬,双手掰开那桃红两瓣,牝口犹鱼儿嚼水般一张一翕,爱煞人也!
花聪见状,喜不自胜,捻住阳物,置于户口。用力一顶,那硬梆梆物儿已彻头彻尾,连根没入,直抵花心。琼英叫爽,周身酥痒,心中如刺,口内伊呀作声。花聪畅然,随即深深浅浅抽送起来,约有七八百下,琼英兴念更狂,躬起柳腰,前耸后顿,着力迎凑不歇,花聪见他如此骚发,淫火大炽,搂住琼英那细白肥臀,狂抽猛捣起来,刹时千馀开外,弄的琼英身儿摇荡,梅树乱动,落英纷纷离树,悠然若雪。
且说那玉月,偶见后园而过见梅树摇荡不定,不知何故,信步走进花园梅树丛前,忽闻唧唧之声不断,不知是甚响,甚觉有趣,遂潜身于花丛后,探头欲觑个究竟。
蹲倒身儿定神一看,方知是哥嫂在行那云雨之事。登觉脸儿一红,热得滚烫,思忖道:「亏我嫂嫂做得出,青天白日定下,竟做那见不得人的事儿,真羞人哩!」想此转身欲走,又道:「既来之,看看又何妨,况我是黄花闺女,尚未见着哩!莫若一饱眼福,看是如何个弄法。」遂又潜身花丛后,把目细觑。
但见哥哥双手紧搂嫂嫂腰肢,胯间那八寸馀长的肉棍儿,往来穿梭于嫂嫂那私处。嫂嫂淫兴甚狂,星眸紧闭,樱唇微启,口内淫声浪语,喧叫不住,要紧之处,不禁大叫几声,刹时惊飞园中飞鸟,还将一头青丝后扬,可谓骚死人了!
亦不多时,玉月觉自家那处做起怪来,思忖道:「连我这小东西也熬不得,难怪哥嫂如此得趣,想必弄那事儿定爽快无比!」一头想,一头探手于档中,摩那私处,不想浪水儿早湿了胯间,滑腻腻的,缩手回来便看,见满把津液,牵牵连连,忙掏了帕儿,揩个乾,又悄悄褪了裤儿,低首觑那汪汪情穴,淫水依旧不住流的可怜,急用帕儿拭,又定睛窥哥嫂云雨。
又见哥哥扳转嫂嫂身儿,令其抱住梅树,躬身将个臀儿后耸,其臀儿又白又嫩,如嫩豆腐般指弹即破。未待哥哥进,嫂嫂急将柳腰软摆,臀儿摇荡,回眸嘻笑,骚达达的,哥哥握了阳物,掳扬了一回,方才照准那肉馒头正中一点红处,挺身用力戳去,哥哥那物儿刹时全军覆没,深陷皮肉阵中,未等杀,闻吟吟笑声一片,玉月愈发觉着有趣,但不知嫂嫂为何知得心花大开?欲知后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三回花二娘巧计私会
诗日:
可惜月年易白头,一番春尽一番秋。
人生及时须行乐,没教花下数风数。
蜂忙蝶乱两情痴,啮指相窥总不如。
如使假虞随灭虢,岂非愈出愈为奇。
且说花聪末行抽送,琼英即笑声盈耳,花聪笑道:「心肝,傻笑甚?」
琼英娇声道:「乖乖,你那亲肉儿似长了眼儿似的,径奔花心而去,惹得我痒极,禁不住笑出声了!」
花聪经他这一说,淫心甚炽,遂搂住琼英细腰,三深二浅将起来。
琼英浪劲十足,柔声颤语道:「心肝,亲肉达达,你得我好快活!」那花聪愈战愈勇,腰上发力,管狂耸。琼英双目微闭,樱唇启开,伊伊呀呀肉麻乱叫,又转头吐出丁香舌儿,花聪一头抽送,一头覆于琼英背上,将口凑过去,含住丁香舌儿,大吮大咂。二人你来我往,吞进吐出,唧唧有声。
琼英觉阴内骚痒,遂反手探于胯间,轻抚那小穴儿。花聪将身直起,往来驰骤,琼英迎凑不迭,连声叫道:「啊呀好快活,死也死也!」花聪闻罢,更是施展平生本事,狠干一遍,不及百馀,竟熬禁不住,遂洋洋大矣。又覆于琼英背上,双手握住酥乳儿,摩抚良久,方才抽身立定。
琼英淫兴未尽,遂坐于春凳上,两股掰开,露出那鲜红红一道肉缝儿。花聪见状,遂取来酒壶酒盏,将酒盏置于牝下,紧贴牝口,又拿起酒壶,将酒倒入牝中,盛满一流而下,溢满酒盏,花聪嘻笑不止,端起酒盏,仰首一饮而尽,道:「好味,好味!」
如此这般,连饮数杯,见壶中无酒,方才罢手。琼英先初牝户骚痒,经酒一浸,便不痛不痒,遂高竖双腿,将牝户启得大开,花聪即蹲身胯间,把口凑去,含住嫩穴吮咂不住。俄尔,琼英下得凳来,花聪坐将上去,琼英将其股一搿,亦蹲倒身儿握住阳物,连亲四五下,便道:「亲肉儿,你的我好快活。」一头说一头将阳物满含,犹仔猪吃奶般吞进吐出。
回文再说那玉月,偷窥良久,浪水儿早将亵衣打湿。阴中奇痒,犹千百蚁子钻拱,试着将一指挖入,往来抽插,不想愈弄愈痒,索性又加一指,二指并入,抽送少顷,勉强杀掉三分火,正淫兴大动之际,忽闻母亲叫喊,不得已抽手束裤整妆,方才悄悄步出花园,寻母亲而去不题。
那花聪二人尽兴之后,各自穿衣整裤,在园中又游玩多时,方才回屋去。
且说光阴荏苒,不觉半年过去,花聪整日无所事事,经街坊上闲耍,结交了一个单身光棍,姓朱名仕白,年有二十五六,专好赌钱监饮,诱人家儿子,哄他钱使用。与花聪相交已久,又着他哄骗了。回家交钱财拿去花费,不出一月,竟用了个光,无奈又将妻子的衣饰暗地偷去卖了花费。不想琼英一日寻起衣来,没了许多,明知丈夫偷去花费,遂禀明了公婆。还剩了几件衣物,送与婆婆藏了。
公婆二人闻知,好生气恼,又拿他没法儿,终恨成一病,两口恹恹,俱病卧于床。好个媳妇,早晚殷勤服侍,并无怨心,又着玉月请了郎中,服药调治,却无效。这花聪犹陌路人般,竟老着脸又去要妻子衣饰,见没得与他,几次发起酒颠,把琼英惊得半死。
花聪没了钱钞,朱仕白甚是冷淡,遂又去寻个书生,姓任名相,年纪未上二十,他父亲在日,是个三考出身,后做了任典趁得千金。父亲亡过,止有老母、童仆在家。妻子虽定,尚未成亲。故自往城外攻书,曾与朱仕白在亲戚家会酒,有一面之交。
是日,二人途中不期而遇,叙了温寒。恰巧又逢花聪,各叙各姓,朱仕白竟一把扯了两个,至一酒楼做一薄薄东道,请着任相,席上狂三道五,甜言蜜语,十分着意。
且说这任相,是个小官心性,一时间又上了他的钩子,次日便拉了花朱二人酒肆答席,三人契同道合,竟不去念着之乎者也了,终日思饮索食。
花聪本是好酒之徒,故终日亲近了这酒肉弟兄,竟不想着柴米夫妻。
父母一日病重一日,哪医治得好,花成春竟一命呜呼了。这花聪又不在家,央了邻家,四处寻觅,方得回来,未见哭了几声,三朝头七,倒方亏了任朱二人相帮。人殓出殡,治丧料理,不期母亲病重,不出几日亦亡。自又忙了一番,方才清.馀剩得些衣衫首饰,琼英又难收管,尽将去买酒吃食,使费起来。这番没了父母,花聪更加放肆,顾不着妻子并妹妹,整日于外鬼混。
一日,朱仕白出主意道:「我三人虽非亲生骨肉,必要患难相扶,须结拜为弟兄,方可齐心协力。我年纪痴长,得做长兄,花弟居二,任弟居三,不知二位弟兄意下如何?」花、任同声道:「正该如此。」言罢,三人吃了些酒,从此穿房人户。
朱仕白唤琼英叫二娘,任三叫二娘做二嫂,与同胞兄弟一般儿亲热。
二人常往花聪家,与琼英、玉月甚熟。这朱仕白见花二娘生得貌美,十分爱慕,每每席间将眼角传情,花二娘并不于理睬。任相青年俊雅,举止风流。二娘十分有意,常将笑脸相迎。任三官虽明白几分,亦极慕二娘标致,因花二气性甚刚,且有玉月随时在家,倘有风声,反为不妙,故未贸然行事。
一日,玉月去姊家玩,花二于家买了酒看,着妻子厨下安排。自家同朱任二弟兄在外厢吃酒。席间,酒觉寒了,任三道:「酒冷了,我去暖了拿来。」
言罢,即便收了冷酒,竟至厨下取酒来暖,不想花二娘私房吃了几杯酒,那脸儿如雪映红梅,坐于灶下炊火煮鱼。任三要取火暖酒,见二娘坐于灶下,遂道:「二嫂,你可放开些,待我来取一火儿。」
花二娘闻罢,心下有些带邪的了,佯疑起来,带着笑骂道:「小油花怎的说话,来讨我便宜幺?」
任三思忖道:「这话无心说的,倒想邪了。」遂将花二娘细看一回,见他微微笑眼,双颊晕红,一时欲火大起,大着胆儿,老着脸儿将身子捱到凳上同坐。
花二娘把身儿一让,与任三并坐了,任三知他有意,更胆大起来,遂将双手去捧过俏脸蛋儿,花二娘微微含笑,便回身搂抱,吐过舌尖,亲了一下。
任三道:「自相见那日,想你至今,不想你恁般有趣的!怎生与你得一会,便死也甘心。」花二娘风眼乜斜,笑道:「这有何难,你既有心于我,须出去将你二哥灌个大醉,你同朱仕白同去,我打发二哥睡了,你傍晚再来,遂你之愿,可否?」
任三道:「多承嫂子美情,要开门等我,万万不可失信!」二娘点头应允,任三喜不自胜,忙换了壶热酒,一并煮鱼拿到外厢,一齐又吃,任三有心,将大碗酒把花二灌得东倒西歪。
天色将晚,朱仕白道:「三官去罢。」任三佯装相帮,收拾碗盏进内,与二娘又叮嘱一番,方出来与朱仁白同去。二娘扶了花二上楼,与他脱衣睡倒,又重下得楼来,收拾已毕,出去掩上大门。
未等二娘回身,便闻叩门声,知是任三又至,忙启门相迎,反将门栓住,道:「可轻些走。」一头说一头扯了任三的手,走至内轩道:「你先坐于此,待我上楼看他一看便来。」
任三早忍耐不得,急扯住二娘手,道:「何必又去,量他不会醒!」
遂拽二娘入怀中,那顾得绸缪,便将二娘推于春凳上,三下两下替他脱去裤儿,两眼紧觑二娘那话儿,又急脱下自家裤儿,露出那又粗又长的阳物。
二娘见之,心下暗喜,思忖道:「不想年少,家伙却甚大,比及丈夫还长三四寸,如今可谓遇着对头了!」那任三早提起了二娘的双足,架于肩上,挺着那尺把长阳物,照准那鲜红肉缝儿刺去。因牝户乾涩,又兼阳物粗长,故紧涩难行,进半个龟头。
任三正欲强行进入,二娘急道:「莫急!想必心肝初行此事,不甚明了!」任三笑不语,二娘将阳物拔出,取了把津唾,涂抹于龟身,方将龟头纳于户口,令任三再行插入。
任三闻罢,点头称是,腰下发力,叱一声,已进入五寸馀,二娘叫爽,直令任三再往里,任三鼓足气力,往前又一耸,趁那当儿,二娘亦将牝一迎,这一迎一耸,刹时那阳物没根没脑全进了去。二娘觉那物儿似直插入了心底,爽快异常,道:「心肝,奇哉,不想年少却生得这般妙物,又粗又长,险些将老娘死了哩!」
任三道:「怎会的,如今我要让你吃个够,也知我这宝物的过人之处!」一头说一头大干起来,未及百馀下,便了一股,一时心软,二娘笑道:「不想你这东西中看不中用哩!」
任三道:「你且等着,是我猴急了,故禁忍不住,便了!」说话间,那物儿又硬,如先时一般挺坚,任三捻住阳物,又欲扎入,二娘道:「心肝,自古道:心急吃不着热豆腐!干这事儿,也是有个路数的,莫再乱冲乱撞,由慢及快,由外及内,那才有趣哩!」正说间,忽闻有人大叫琼英名儿,不知何人,且看下回分解。
第四回佳期两下情浓
诗曰:
古时男女说亲迎,来世风流妄绵情。
桃花星是命中照,故今才郎打粉乔。
任尔说明多不忌,阳台暮暮与朝朝。
嫂既多情非更妖,弟将云雨来拔撩。
且说二娘正与任三传那房中之术,忽闻有人叫「琼英」,二人停住,侧耳细听,方知是花二梦呓,遂又重赴巫山,任三又行刺入,经二娘如是一说,便也知其几分,遂款款抽送,行那三浅一深之法儿,往来五六百馀,牝中淫水渐生,愈来愈滑溜如润,二娘痒极,一时间酥了半边身儿,即双足控紧三颈儿,口内伊呀淫声不绝。
任三知他有些好意思了,遂大抽大送,似渴龙饮井,又如饿虎擒羊,刹时就有千馀下,弄得啧啧有声,二娘知他要了,急探手扯住阳物,令其紧抵花心,方才了少许,在牝中稍停片时,又急急抽送起来。
二娘已至佳境,户内浪水儿流个不住,口中淫声浪语又大起,任三恐惊醒楼上花二,遂将手掩其口,二娘知趣,将个牝户管往上迎凑,任三见他如此美貌,又甚淫骚,愈发狠干,拼力命狂捣,不顾捣碎了花心,更不顾折断阳物,又大有千馀下,二娘爽利之极,心肝肉麻乱叫,四肢乱舞。
任三亦觉心欢,管猛力抽送,竟不知阳物软缩,而反憎二娘牝大,即是如此,亦不完局,小休片刻,阳物于牝中又硬,任三甚喜,一头徐徐抽耸,一头覆于二娘肚上,道:「我的心肝嫂子,今日快活否?」
二娘神酣兴举,忙展玉腕相抱,道:「乖乖亲肉儿,的我快活死了。」
任三闻罢,暗自幸喜,思付道:「莫如趁此时,与他下马利害,日后亦可尽情享用。」遂放开手脚,急抽深投,的牝内浪水儿汹涌不止,唧唧乱响,二娘亦双腿倒控于任三腰上,大力奉迎任三,任三道:「好嫂子,我比二哥如何?」
二娘遍体爽美,娇喘微微,道:「他是粗人,怎能与你相比?奴与君一次,胜他一年。」
任三大喜,遂抱起二娘,道:「心肝,你我去床上弄去。」一头说一头已至床沿,即置下二娘,将身儿横陈于床,自家立于床沿架起金莲,又扯过绿枕,衬于二娘腰下,挺枪大肆侵入,阳物于内拱拱钻钻,若鹅鸭咂食之声,二娘花心被弄碎,昏去又醒,醒来又昏,悠然如在浮云,身儿更如狂风拂柳,淫声一浪高比一浪,大凑大迎,又有个把时辰,二娘精尽力竭,忙道:「心肝,累死我矣,待你我歇上一歇。再干如何?」
任三怜他娇媚,遂拔出阳物,上床并头而睡,任三把手捻那对玉乳儿,又将二娘通身摩了个遍,细嫩光滑,柔若无骨,遂道:「乖嫂子好个丰满的乳儿。」
二娘乜斜凤眼,探手于任三胯间,捻住那粗硬阳物,抚摩多时,道:「心肝这物儿煞是利害,弄的我一佛出世,二佛升天,几欲昏死过去。」
任三道:「你那美物儿,遇着我这宝物,亦是你的福份。」二人调笑一阵,不觉口乾舌燥,遂起身下床,取了果品同吃。
任三拿了一个大果,笑道:「嫂嫂的果子好大哩!」二娘沉吟片时,笑道:「还没你那龟头大哩!倘若不信你比上一比!」
任三急道:「比又何妨!」遂按倒二娘,将两股掰开,趁势将果子向牝户塞去,不多着力,竟全陷了进去不见了影儿,任三心中老大着忙,探手拿他不得,遂令二娘蹲倒身儿,以手扣其臀,良久方才落出,任三拾起果子,吃将起来,道:「好吃,比及一般果子不同!」
二人话到浓处,兴又动举,双双登床入榻,重摆战场,再又对垒,那二娘跪于床上,任三从其臀后插入,直捣黄龙,旋即狂抽猛扎,一口气千馀下,二娘觉他不胜力气,遂一个黄龙转身,将任三仰置于床,继尔跃马而上,将那阳物照准牝户,坐将下去,叱的一声,止进大半截,研研擦揍,方才全根没入,旋即一起一落,桩套不止。
任三在下,亦举枪相迎,你来我往,刹时又是千馀下,时值三更鼓响,二人方才罢手,收拾整衣毕了,二娘道:「不想此事恁般有趣,今朝方尝得如此滋味,若能常常聚首方好。是朱仕白这,每每把眼调情,我佯做不知,不可将今番事漏些风声与他,那时花二知晓了,你我俱无命矣!」
任三听罢,心下暗喜,道:「蒙亲嫂不弃,小弟感恩不尽,怎肯卖俏行奸,天地亦难容于我。」
二娘道:「谈何恩何情,常相往来,亦落得个你我受用,大家快活,但不知几时又得聚会?」
任三道:「自古郎如有心,那怕山高水深。」
二娘道:「今夜欲与你同眠,料亦不能。夜己将深,不如且别,再图后会罢。」
任三道:「既如此,再与你做耍会儿。」一头说一头又脱去二娘裤儿,掏出阳物再赴阳台,不想花二睡醒,叫二娘拿茶。
二人急急如惊弓之鸟,二娘忙回道:「我拿来了。」遂悄悄送着任三出去,拴好大门,送茶与花二吃了,花二道:「你怎的还不来睡?」二娘道:「收拾方毕,如今睡也。
次日天明,花二又去寻着朱仕白,同去会任三官。恰巧任三官在家,见花朱二人来家,便随口儿道:「昨晚有一表亲,京中初回,今日老母着我去望他,想转得来时,天色必晚了。闻知今海边,有一班妓女上台扮戏,可惜不得工夫去看。」
花二道:「既有如此好事,何不同去观了,再回身望亲去?」任三官忙道:「老母之意,岂敢不从,莫如你二人先去,待我望了亲,若时日尚早,我急赶来便是!」
二人听罢,亦不勉强。花二对朱仕白道:「朱大哥,既如此,你与我去观戏何如?」
朱仕白道:「去到不怎的,倘然没戏,是空走这多路途何苦!」
花二沉吟片时,拉住朱仕白道:「我有一旧亲,住在海边,若无戏看,酒是有得吃的,去去何妨。」朱仕白亦是好酒之徒,听说个酒字,一时间来了精神,嘻笑道:「既如此,同你走一遭,这便早早别了罢!言罢,三人一哄而散。
不说花朱二人被任三哄去,且说任三又至房中,取了些银子,买办些酒食,拿上径去了花二家,立于门首,叩门而进,见了二娘便笑道:「他二人方才被我哄去海边了,一来往有三十馀里路。即是转回,料天已暗了,如今备了些酒果在此,且与你盘桓一日。」
二娘道:「如此极好。」遂急把门掩上,任三炊火,二娘当厨,一时间都已完备。二娘道:「我二人若无远虑,必有近优,倘你哥哥一时来家,也未可知,若被撞见,如何是好?」
任三道:「嫂子说的在理,常言道不怕一万,怕万一。是小弟一时想不出个法儿来,依了嫂子便是。」
二娘笑道:「不愧为任三官,话儿甜嘴儿蜜,向日公婆后边建有卧室一间,终日关闭至今,且是僻静清洁。我想起来,到那边吃酒欢会,料他即回,亦不知晓。你道好幺?」
任三听说,欢喜至极。即时往后边,开门一看,里边床帐桌椅,件件端正,打扫得且是洁,壁上有诗一首,道:
轩居容膝足盘桓,斗室其如地位宽。
壶里有天通碧汉,世间无地隔尘寰。
谁人得似陶天亮,我辈终惭茕幼安。
心境坦然无窒碍,座中好着蒲团。
毕竟不知后来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五回玉月偷听嫂奸情
诗曰:
千里姻缘仗线牵,相思两地一般天。
驾信那绍云引报,梅花诗勺陇头传。
还愁荏苒时将逝,恐年华鬓渐翻。
此昼俄闻应未晓,忽忽难尽笑啼缘。
却说任三将诗看罢,即摆酒肴果品于桌上,二人并肩而坐,你一杯,我一盏,欢容笑口,媚眼调情。自古道:「花为茶博士,酒是色媒人。」
调得火滚,搂坐一堆,就在床上取乐起来,今番与昨晚不同。怎见得不同?见:
雨拨云抹,重整蓝桥之会。星期月约,幸逢巫楚之缘。一个年少书生,久追无妇之鳏,初遏佳人,好似投胶在漆。一年青春荡妇,向守有夫之寡,喜逢情处,浑如伴蜜于糖。也不尝欺香翠幌,也不管挣断罗裳。
正是:
甫将云兵起战场,花营锦阵布旌枪。
手忙脚乱高低敌,舌剑唇刀吞吐忙。
二人欢乐之极,满心足意,整着残肴,欢饮一番。二娘道:「乐不可极,如今你且回去,后会不难了。」
任三道:「嫂子在理,要你我同心,管取天长地久。」言罢作别,竟自出门去了。
不多时,花二已回,二娘见了,暗自思忖道:「早是有些主意,若迟一步,定被撞个正着。」自此之后,任三官便不与花朱二人日日相共,寻着空儿便与二娘偷乐。若花二不时归家,他便躲入后房避了。故此两个未撞见,见朱仕白乃个大老倌,甚是没兴,遂常撞至花家里来寻花二。
一日,花二不在家,门是掩上的,朱仕白便径直撞入内轩,问道:「二哥可在家幺?」二娘知是朱仕白,遂没好生气道:「不在家。」
朱仕白觉着那娇滴滴话声,登时淫心萌举,一时间腰间那物儿直竖起来。常有此心,奈花二碍眼,今闻得不在家中,遂壮着胆儿,去至里面道:「二娘见礼了。」
二娘见他进了来,亦不便拒他,答礼道:「伯伯外边请坐。」
朱仕白笑道:「二娘,几时兄弟在家,我倒常在里面坐着。幸得今日兄弟不在,怎生得打发上边去坐!二娘,你这般标致人儿,我已爱慕久矣,如今天赐良机,你倒怎先说出如此不识趣的话来!」
二娘闻罢,急正色道:「伯伯差矣,我家男人不在,理当外坐,怎生倒胡说起来?」
朱仕白心中如火,登觉周身燥热难耐,遂大胆走过去要搂,早被二娘一闪,到了外边来,怒气陡升,脸儿涨得通红,恰花二撞见,见二娘面呈怒色,忙问道:「娘子为何着恼?」
二娘尚未着答,朱仕白听得问话,遂闯将出来。花二见状,满肚子疑窦。二娘走了进去,花二忙问道:「朱大哥,为着甚事,令二娘着恼?」
朱仕白急释道:「我因乏兴,寻你走走,来问二娘,道你不在家,我疑他哄我,故意假说,遂及里面望望,不想二娘嗔我,故此着恼。」
花二是个耳软的直人,竟不疑着甚的,亦不去问妻子,遂对朱仕白道:「大哥,妇人家心性,不要责他,这厢与你街上走走去罢。」一头说一头扯住朱仕白,并肩而去。直至二更时分,花二方回,二娘见他酒醉的了,欲待说起,恐他性子发作,连累自身,故得耐着不言。
次早,见花二不曾起来,不敢开口。朱仕白自此不敢来寻花二了,又花二常在家,倒便宜了任三,日间不消说起,至于花二更深不回,任三则常伴二娘,即是花二来家,亦十有八九是醉的了。故此二人甚是高兴,每每服侍花二去睡,花二亦不想寻二娘行那云雨之事,故此二娘倒与三官弄得十分畅快。
这日,花二又不在家,走时道明晚上不归了。任三与二娘酒足饭饱毕,又并至后房行那云雨事,恰玉月自表姊家回,见屋中无人,且门全开着,料走不远,遂绕过正房,穿越花园,竟至后房门首,忽闻里面气喘声急,不时有嫂子浪语淫辞,遂绕至房后,立身贴耳细听,思忖道:「哥哥自与那帮酒肉兄弟搭上,竟与嫂嫂房事稀疏,怎的今日如此亲密,莫不是嫂子耐不住寂寞,有甚奸情乎?」
想此,忽闻得一男人道:「心肝,二哥与玉月不在,倒便宜了你我,日夜尽享人间至乐,好不痛快!」又闻嫂子道:「乖乖亲肉,今生跟上他,是我的晦气,每每我欲云雨,他则冷水烫猪般死不来气,那时真熬得慌,一时竟以指相替那物儿,虽不尽兴,倒亦能杀掉三分火。」
玉月这才晓得,原来那男人正是哥哥拜把弟兄任三,即叹口气道:「也难怪嫂子偷人养汉,正值青春年少,哥又常疏云雨,哪能熬得。」又偷听良久,见没了甚响动,方才轻手轻脚离去,回到自家房中。
不多时,见嫂子亦至前房,鬓发蓬乱,遂上前故意问道:「哥怎的不见了?」二娘支吾道:「你哥老早就出去了,不曾在家。」
玉月追问道:「方才你与他不是在后房幺?」二娘刹时慌了,急道:「适才你都听见了?」玉月笑而不语,又道:「此乃哥的不是,嫂子如此之为,尚在情理之中。」二娘听他这幺一说倒也心宽几分,道:「好姑子,千万莫与你哥讲,若走漏风声,我与任三皆命不保。」玉月道:「嫂子且放心,末敢与他说之!」言毕,二人下厨整治晚饭。
这二娘虽听玉月如是说,仍有几分疑心,想道:「非如此如此,这般这般不可。」遂趁机溜进后房,与任三道:「心肝,你我之事不意被玉月听见了,恐他向花二说起,得想个法儿塞住其口。」遂将计与那任三说了,任三连称妙计,二人商议好,二娘重回灶下。
是夜,二娘玉月二人吃罢晚饭,玉月觉困,遂起身回房睡去,二娘扯住道:「好姑姑,是夜你哥不归,我与你睡去,如何?」
玉月道:「既如此,又何尝不可,况我一人亦寂寞,无人相伴。」言罢,二人并至玉月房中,脱衣上床,并头而眠,二娘道:「姑娘好生标致,我若是男儿身,定爱死你时!」一头说一头将玉月身儿摩了个遍,复又摩那丰隆柔润的化户,俄尔,丽水儿溢了,粘连滑腻,玉月似觉爽,两只小腿儿张缩不住。
二娘道:「姑姑可熬得?我如你这般年纪,早春心飘发,每每听见别人干那事儿,心儿就痒起来,着实熬不得。如今,你哥常不如我意,无奈借一件东西杀火受用。名曰于东膀,比男人之物,亦有几倍之趣,妙不可言,对门那青年寡妇亦常来借用,拿去取乐。」
玉月急道:「无人在此,你拿了我一看,怎生模样一件东西,能会作怪?」
二娘道:「姑姑,此物古怪,有两不可看,白日里不可看,灯火之前亦不可看。」
玉月笑道:「如此说,终不能入人之眼了?」
二娘笑道:「惯会入人之眼。」
玉月又道:「我讲的乃是眼目之眼。」
二娘道:「我亦晓得,故意逗着耍的。」
玉月被他说这一番,心下痒极,又思忖道:「莫非骗我?」遂推他几推,道:「嫂子,可曾睡?」
二娘道:「怎的能睡去,春心难来,如何可眠?倘若你我是一对男女,干起事来,不甚爽利幺?」
玉月道:「既如此,你那件东西何不拿来相互一试?」
二娘心下暗喜,知他上钩,遂道:「如此说,姑姑不可点灯。我这即拿去。」遂披衣而起,出门去了,不知后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六回风流郎勇战双娇
诗曰:
瞥见英豪意已娱,几番云雨入南柯。
芳年肯向闺中老,绿鬓难教镜里过。
纵有奇才能炼石,不如素志欲当炉。
度尺天涯生相隔,断肠回首听啼鸣。
且说二娘出门,径直去了后房,领了任三出来,紧随其后,并至玉月房中,双双登上床榻,玉月道:「嫂子,那物藏在何处?」
二娘道:「今把藏于我的里边,极有人性的,若是高兴,就在里面挺出,与男子那物几无二。」
玉月笑道:「委实奇怪。」言罢,二娘将玉月按仰于床,掰开双股,即见玉月嫩穴,将中指探进其内,轻挖一阵,又拨着花心,动了几回,淫水淋淋流出,遂暗将任三让前,挺那坚硬阳物,置于牝口,二娘遂道:「姑姑,我往里入了。」
任三闻得,将身一挺,已进小半,原来经二娘弄过,兼阴水甚多,故此轻易进了。玉月初次开苞,未免有些疼痛,遂推住任三肚腹道:「嫂子,痛死我了,不干了。」
二娘道:「姑姑忍着,我缓缓进入。」那任三遂拿开玉月的手,又着力猛的一耸,叱的一声,早连根进入了,任三兴急,着实大抽大提。玉月哪知真假,不管三七廿一,搂住任三腰儿,柳腰轻摆,伊呀有声道:「可惜你是妇人,若是男人,我便叫得你亲热。」
二娘一旁道:「何妨且当做男人,方得适兴。」玉月道:「倘你变做男人,便偷个空当留你于房中,与我尽情受用。」二娘见他如此骚发,道:「姑姑,手把此物摩他一摩,可像生的幺?」
玉月闻罢,将手去根边一摩,果是生着根的,且滚热如烙,知是男子身儿,忖是那任三,遂急道:「中你们计了。」
二娘知事料难隐瞒,道:「姑姑,既至如此地位,何不弄个周身畅快?」一头说一头下得床来,掌上灯烛。玉月一看果是那任三,本想抽身扒起,却不意酥了全身,怎忍抽身,索性双腿倒控任三之腰,口内哼呀乱叫,将个肥臀耸摆。
任三见他这骚达达的光景,越发狠干,扯过绿枕,横于玉月腰下,推起金莲,着实抽送,刹时千馀开外,淫水四溢,缘股而下,合着殷红血儿,湿了绣被,狼藉一片。
玉月周身骚痒,体酥骨软,畅快异常,顾不了疼痛,娇声浪气道:「我的心肝,那面酸痒难禁,你且尽情驰骤便是。」
任三见他如此骚浪,兴若酒狂,索性大抽大送,约莫五六百下,玉月如升仙般,云里雾里,口内亦心肝宝贝肉麻淫叫不迭,下面一片淫水响,将那玉臀一抬一放,极力迎凑。
任三因着力过猛,竟无疏缓馀地,体力不支,抽送的度数减慢。玉月正渐近佳美之地,嫌其抽送徐缓,甚不觉爽,遂翻身扒起,骑跨于任三身上,将牝照那硬生生阳物,吐的往下一桩,登觉爽遍全身,那物儿早身陷肉阵,并无退路,遂将身如来千里之驹起落不定,桩套起来。
任三大仰,任他着力大弄,省些气力。玉月越桩越猛,肌肤相撞,乒乒乓乓直响,口内淫语喧天,淫水儿滔滔而下,刹时八百馀桩。玉月双目紧闭,手扪酥乳,骚态十足,爱煞人也!
少顷,任三重整旗鼓,驾起威风,腾身而起,玉月顺势仆倒,任三将其臀捞起,令其跪于床栏,即蹲身其后,将阳物照准那妙品,猛力刺去,阳物紧紧抵定,双手抱住腰肢,管尽情抽送,玉月身儿摇漾,二娘执烛在手,向前笑道:「心肝我儿,这会也够受用你了,怎不放温柔些,尽老力于此行事,我姑是娇花嫩蕊,何以经住狂风骤雨?」
玉月被的有气无力,开口道:「嫂子在理,我那话儿未曾经风雨,应怜惜我才是!」
任三领命,却耸身直抵花心,又一阵大抽大送,可谓箭无虚发,皆中花心。玉月连声哀告道:「饶我罢,死也!死也!」身儿一抖,丢了阴精,四肢骤冷,舌卷气缩,气喘嘘嘘,不能叫唤,低头落颈,瘫软于床。任三这才洋洋大,休兵息战。
二娘将玉月款款扶起,玉月不觉满脸羞惭,措身无地。二娘道:「你这个蛮子,倚着有些本事,将姑姑恁般摩弄,实为可怜。」玉月勉强翻身,奈何腰胯酸痛,不能俯仰,遂至床里侧,面朝外侧身微屈而卧。
任三这当儿下得床来,取了酒,自斟自饮,几杯下肚,酒性大作,周身燥热,刹时阳物又硬橛橛的昂扬而立,遂走至床沿,扯住二娘双腿,将阳物一扶,老马识途一溜而入,耸身大弄。
二娘乃是身经百战,久经沙场的宿将,焉能适兴?反以双足紧控其臀,着力帮衬,道:「心肝,爽也,速些,再速些!」
玉月在旁观得仔细,思忖道:「不想嫂子是风月场中班首,二人如乾柴就着烈火,越烧越旺,我哥常在外鬼混,难怪嫂子偷汉子,料想如此劲头,他也难熬得。」遂微展双足,静观其战。
任三愈战愈勇,二娘越弄越骚,你耸身大弄,我拼命相迎,刹时千馀度,弄得浪水儿四溢,乱响一片,好不骚得爆火。
干了个把时辰,二娘道:「贤弟,你我弄个羊油倒浇蜡烛罢!」一头说一头扯住任三上床,令其仰卧,又将绣被扯过,衬于腰下,遂翻身上马,策鞭急驰,不上千回,二娘连丢数次,任三禁忍不住,亦一喧而出。
事毕,三人并头贴身而卧,任三居中,左拥二娘,右抱玉月,说笑片时,即昏昏睡去。次日天明,玉月先醒,见二人依旧睡意正酣,遂急推醒道:「还不速起,恐来人撞见,那可不好看了。」
言罢,三人同披衣而起,玉月经任三一场翻天动地的干,阴户已肿个不堪,疼痛难忍,不能直起身儿行走,遂被二娘背着,去了回茅房,又回床养息。
任三见这光景,生起怜惜之心,至床沿亲了玉月几口,道:「俏心肝,可苦了你,都是我孟浪,这里有消肿的药,敷些于其上,好好将息。」
一头说一头揭开被儿,见那话儿肿得高凸紫红,二娘替他抹了药,又将被盖了,二人方才出去将门带上。
那二娘笑着即对任三道:「你可干得,险些将小姑死哩。这下可好,你那乖肉儿得往一边放了。」
任三笑道:「不是还有你幺?」二娘道:「死贼囚!竟说此话。」
任三道:「若是死了,何人令你爽利?」一头说一头走近二娘,搂抱住将口儿凑过去,二娘亦不躲闪,吐了丁香舌儿,度于任三口中,胡乱搅了一番,任三又吐过舌尖,二娘含了大吮大咂,如此这般,吞进吐出,你来我往数回。
二人调得火滚,情欲难禁,亦不顾许多,索性就地干了起来。任三推二娘背靠于,将其裤儿褪至膝间,又解了自家裤儿,露出直矗阳物,朝二娘股间乱戳。惹得二娘牝内酸痒难究,浪水儿牵线般流下,急道:「管乱戳做甚,还不速干了完事,如若有人觑见,岂不羞杀人。」
任三听了,这才挺身直射而入,直达花宫,妙不可言,欲行抽送,奈何二娘矮些,任三不便用力,遂掇了春凳,垫于二娘脚下,方与任三一般平齐,这才二快三慢,忙忙的一通抽送。
摩转百馀度,任三兴急,突的猛耸起来,那二娘不备,脚下摇摆,竟滑跌下来,那物儿却滞于牝中,经他身一牵,险些将阳物拦腰折断。
任三直呼其痛,亦无心恋战,遂草草完局。收拾妥当,对二娘道:「心肝,我已数日未归,如今已值正午,我须回家一趟,不多日再来会你。」
二娘道:「也好,况今日花二来家,若撞见恐生事端,是不出二三日即来,莫让我受那有夫之寡的煎熬。」任三应允二娘遂引至后门,二人搂住又绸缪一回,任三方才不舍离去。
二娘转身回至前堂,忽见花二回来了,二娘急理鬓整衣,出来相见,不知后来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七回乔妆改扮破花心
词曰:
倒风颠鸾堪爱,肚下悬巢相配。不是情娇花,怎把玉杵高碓,亲妹,亲妹,蜡烛烧成半对。
且说任三刚走,花二即归家,问二娘道:「妹妹已归幺?」二娘道:「正是。是这厢头痛,睡着哩!」花二听说,急奔玉月房里,揭开罗帐,道:「妹妹可好些幺?」
玉月道:「哥哥不急,已无甚紧要的了。」待花二出门,玉月即披衣起得床来,把那云雨之乐又忆想一回。
且说那二娘见天色晚将下来,遂下厨整了酒肴,三人吃罢,闲聊一阵,即各回房中睡去。
一日,花成春的百日之期,家中设于素宴,招待来客,那花二的表妹春梅亦至,是夜待宾客散尽,花二一家并春梅同坐吃酒,席间,四人谈笑风生,推杯换盏,好不闹热。
且说这花二,数年不见春梅,今日一见,爱慕不已,不想表妹竟出落得如此标致,怎见得?但见:
蛾眉带秀,凤眼含情,腰如弱柳迎风,面似娇花拂水,体态轻盈,汉家飞燕同称,性格风流,吴国西施并美,蕊宫仙子谪人间,月殿嫦娥临下届。
花二看得心下痒痒,坐立不是。常言道妇人眼尖。春梅一眼便识出,遂道:「表哥今日怎的,数年初逢倒像坐不得了,想是有甚心事不成?」
一头说一头将那骚骚的眼光看那花二,嘻笑不止,引得众人皆笑将起来。
少顷,春梅道:「表妹长大了,且越发的标致了,可曾有人来求亲幺?」
玉月笑而不答,倒是花二接话道:「城里李举人来求过了,是不曾下聘。」
春梅又道:「妹妹生得貌若天仙,舅父母已逝,你当哥的可得替妹做主,寻个好婆家。」
二娘在旁道:「春梅妹妹既如此爱小姑,何不代劳?」言罢四人笑将起来,不觉夜已更深,玉月同了春梅,回屋去睡,花二夫妇收妥残羹剩骨,亦双双睡去。
且说这春梅,人虽上了床,心思却不畅,不能即睡,直至四更鼓响,方才睡去,花二天明起来,于玉月门首徘徊半晌,欲推门进去,怎奈妹子在里又不好进去,恰巧玉月到厨下去,花二见了,心下暗喜,即抽身至玉月房中,揭开罗帐一看,见那春梅睡得正熟。
花二思付道:「她昨日的话有些勾情,且席间眉飞色舞,想必她昨夜未曾睡好,大早还这等酣睡。」欲进前去染指一二,又恐玉月走来。无奈得大胆坐于床沿,把被轻轻挑起,不意那春梅竟是个赤精条条的一个白嫩身儿,低头看那牝户,雪白细嫩,光肥润泽,鸡冠微吐,好似初发酵的馒头。花二看得目摇神乱,忽听有脚步响,忙钻出帐来,见是妹子,遂轻咳嗽一声。
玉月笑问道:「哥哥要来做贼幺?」花二道:「何出此言,不见表妹,特来一看,这岂就是做贼!」
春梅正在梦中,竟被惊醒,见下身的被都不曾盖着,遂问玉月道:「妹妹同何人说话?」玉月道:「是我哥,我去厨下,他正好来看你。」
春梅已知被他轻薄了一回,却不叫声,遂起来缠了小脚,又向夜壶里小解,方才穿衣束带。那雪白身儿,酥胸玉乳,全不遮掩,被花二闪在门外一一觑见,故欲火发动,口水儿沽沽直咽,恨不得合一口清水将春梅吞下肚内。
看倌,你道那春梅此来,为着花成春的百期幺?非也!百期是名,实则早闻表哥英俊,趁时与花二耍上一回,以制春心。孰料玉月碍眼,打搅了他的美事,春梅心中暗恨一回……
是夜,春梅道:「我明日即归。」又把接玉月玩耍几日的话说了,玉月与哥嫂皆许,那花二故意道:「表妹次早归去,何不让我送你,亦好去你家掰个门槛。」春梅笑道:「表兄这等闲,同去便是。」
次早,春梅家着人抬了轿子来接,道:「老爷等小姐回去。」春梅听了,忙着梳洗,去时,春梅对花二夫妇道:「后日我着人接妹子去。」玉月道:「不知怎的,忽然头痛起来,恐去不成了!」春梅未曾听见,竟上轿去了。
三日过去,遂着人来接道:「我家小姐特来接你家小姐过去。」孰知春梅去后,玉月便不能起床,那二娘正要回他,花二道:「我与妹子一般面貌,一样长大,脚儿大了些,可将妹子新做的花衫裙并将暂饰,与我穿戴了,亦像妹子模样,可替妹子前去。」
二娘思忖道:「此计甚妙,且他去后,我又可与任三干那勾当,岂不正好!」遂应允了,又与玉月商议,取了钥匙,开了梳匣,与他改作女妆。梳了牡丹头,燕尾鬓,插上首饰。把件红绉纱袄儿穿了,又着一领鸦青锦绣花衫子,下系八幅红裙,把脚儿遮掩。打扮停当,宛然是个玉月。
玉月相看,道:「像是像,去时要走那莲步。」花二把镜一照,笑道:「天既生我以如是之貌,何不令我变做妇人。」
二娘假意道:「你去去就来,休要被人识破,亲情体面上不便。」
玉月道:「哥哥此去,姊姊如何肯放他就来。」言罢,二娘佯做末听见,推花二上轿去了。花二一路心下暗喜,思想如何勾那春梅上手。
到得春梅家,姑父姑母并春梅接出中堂,于春梅房里坐下,吃罢晚饭,闲聊阵子,春梅道:「妹子,同你睡罢。」
花二道:「姊姊先睡,我即来。」
春梅道:「表哥今夜在家幺?」
花二道:「有相好的接他去了。」
春梅讶道:「嫂子怎肯放他去?」
花二笑道:「嫂子不让去,他便耍赖,跪嫂子面前不起,无奈嫂子依了他。」
春梅听了,摇头叹气道:「可惜!可惜!这等美郎君,不知今夜哪个小骚货受用?」花二见他如此婉惜,料对自己有意,遂大着胆子道:「姊姊莫气,我明日叫他来陪你,可好幺?」春梅一笑,竟卸了衣裳,趋进被窝睡去。
花二早见了那雪白身儿和两只酥乳,登时神魂飞越,把持不住。遂一口吹灭了灯,急宽衣解带,上床挨身进被,正碰软玉温香娇躯,心痒难抓,那物儿登时大竖,遂臂枕春梅头,另只手儿摩抚其身,粉颈香肩,玉乳酥胸,肥臀美股,摩了个遍,惹得春梅禁忍不住,气喘急急,搂紧了花二。
花二知趣,扒上春梅身儿。春梅不知何意,遂问道:「妹子,你这是做甚?」花二兴起,亦不他顾,急道:「表妹,我非玉月,乃你表哥花聪也!」
春梅不信,遂道:「妹子乱讲,明明接来的是玉月,还能变成你兄花聪不成?」花二又道:「表妹,倘若不信,你摸上一摸。」一头说一头将手拿了去,向胯间摸去,果是如此,一根肉棍硬若铁杵,热烙有趣,心下喜极,遂道:「表哥,你怎想出如此妙计,竟骗过了姑父姑母,就是我亦认你不出,高明!实在是高明!」
花二道:「妹妹早想与我亲近,却苦于无良机,你说是否?」春梅故意道:「休要得意,谁人属意于你!」话虽如是说,却早酥了半边身儿,把持不得,遂双脚高竖,引得花二淫兴教发,急举枪大击。
春梅年纪才十七,尚是黄花闺女,未免户道紧固难行,故进龟头,又吐些唾津,抹于阳物上,加力一顶,叱的一声,又进二寸馀,春梅呼痛,把手阻住。娇滴滴道:「亲哥,我痛,且待会儿,再不得往里入,进去一半,即如此疼痛,要是全入进了,恐要痛死我了?」
花二那听,假意怜恤一番,乘其不备,忽的扯开其手,猛的往前一耸,方才连根进入,正欲抽送,闻得春梅「嗳呀」一声之后,登时无了动静。不知春梅性命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八回俊俏郎巧取娇娘
诗曰:
空房悲独守,欣遇知意郎;何必相勾引,私心愿与偿;鸾颠凤又倒,哥姐战愈狂。
且说那花二拼力狠,力透重围,春梅痛的钻心,当下昏死过去,花二见无动静,急去点了灯烛,又以口布气,俄尔,春梅方才醒将转来,黛眉紧锁,哼呀不住,启开双眸,哀声叹气道:「亲哥哥,你怎的如此狠,令我险些死了过去。你且稍待片时,等我喘口气儿,再不迟。」一头说,一头双足却勾住花二臀儿。
花二见她这般光景,亦止下来,但手却不放,把玩双乳,玲拢紧挺,如覆玉杯,奶头猩红,犹樱桃般可爱,轻轻拨弄会儿,引得春梅春光发动,虽有些疼痛,早被骚痒所替,遂向上耸了几耸。花二会意,随即款款抽送,行那九浅一深之法儿,不出十馀下,丽水儿渐生,滑溜无比。那花儿又是一番没棱头脑的大干。
春梅登觉牝内火灼般难忍,更涨得难过,不由得身儿颤柳腰酥,连连摇头摆肢。花二愈抽愈急,约有八百馀下,花二兴若酒狂,阳物于牝内乱钻乱拱,的淫水儿横溢。春梅户儿热烙痒极,妙不可言,便道:「心肝,爽死妾了,你且尽力抽送,顶着里面那妙品,爽利得很!」
听罢此话,花二愈发狠干,一口气又抽有千二三百下。春梅已至乐境,心肝宝贝乱叫,下面唧唧淫水响个不住,竟连丢两回,一时周身通泰,畅快无比。
春梅初行云雨之事,户道窄小,将那物儿套得甚紧,花二爽快至极,又竭力抽送数十下,禁忍不住,不觉彪彪的将阳精了个汪洋大海。春梅花心初逢甘露,酥痒难当,将臀儿扇般的摇,伊伊呀呀乱叫。花二使出手段,让那阳物于牝中又硬。
春梅喜极,笑道:「亲哥哥,你煞是会干哩!」花二笑道:「若不会干,怎的让心肝妹子受用?」一头说一头搂住春梅纤腰,翻转身儿,令其跪于床上,将玉股掰开,那肥肥臀儿柔嫩光滑,汪汪情穴红白相间,爱煞人也!
花二急跪其身后,扳住春梅纤腰,照准那汪汪情穴,举枪即刺,浅抽深投,悠然行事。春梅微微含笑,哼哼唧唧,将头转回,吐过香舌儿,把香津喂与花二,花二亦把津唾儿喂与春梅吃,两个思想切切,绸缪无比。
少顷,春梅玉体摇曳,反手扯住其阳物根,直往嫩穴里乱塞,极尽骚淫。花二见他骚发发的,精神狂逸,大抽大送,往来驰骤,刹时二千馀下,拉扯抽拽之声盈耳,弄的春梅淫叫肉麻,将个细嫩臀儿猛掀狂凑,甚是云酣雨洽。
战有一个时辰,春梅遍体全酥,连丢数回,犹如斗败的公鸡,低首落颈,瘫软于床。花二馀兴未尽,又急急抽送数十下,见春梅四肢难举,亦无心恋战,又狂了一回。将春梅双股捞起,见那两片肉儿,早已殷红夹杂,泛溢不堪,遂取了白绫绢,揩个乾,又拭了自家话儿,方才拥着春梅,恣意调弄。
花二道:「心肝妹子,我本领何如?」春梅道:「我长恁大,从未历此妙境,亏你扮了妹子而来!」花二道:「我贪你色,你爱我貌,不得已改妆来会,如令岂不落得你我爽快幺?」二人你说我摩,连呼有趣,恐隔壁丫头小鹃听见,即交股贴肉,紧搂而眠。
次日天明,日上三竿,二人方才醒来,花二下床,穿了衣裳,提起裤腰之际,那话儿几自硬将起来,不料被小鹃于暗地里觑见,思忖道:「明明接的是玉月,怎的长了那肉东西,莫不是她表哥扮的幺?」既而两人梳洗毕,用过早膳,花二与春梅花园对弈去了。
且说这小鹃,早上看了那物,心下生疑,遂趁着空当,悄悄躲于暗处窥探。那花二步至花园,四顾无人,即去小解,岂料又被小鹃望见,那大东西又粗又长,暗笑道:「我道是花姑娘,原来果真是她表哥改扮而来的哩!」
花二溺毕,转身却看见小鹃,知被识破机关,遂跨前一步拦腰抱住走至春梅处。小鹃被唬得面如土色,直求春梅让表少爷放了他。春梅见说,遂道:「小鹃,你都知晓了,事已如此,料难瞒你,切不可说与外人知晓,我自另眼相看你便是了。」
小鹃急道:「小姐不吩咐,也未敢坏小姐名节,何用小姐说来。奴奴自守口如瓶。」春梅听罢,递与小鹃二三两碎银,与花二便个眼色,竟自起身去了。
花二会
男人不识本站,上遍色站也枉然
开元棋牌
PG娱乐城
永利娱乐城
澳门葡京
官方葡京
澳门葡京
太阳城
开元棋牌
澳门葡京
新葡京
澳门葡京
PG娱乐城
PG大满贯
开元棋牌
威尼斯人
PG娱乐城
开元棋牌
澳门葡京
PG国际
开元棋牌
开元棋牌
威尼斯人
大发娱乐
英皇娱乐
官方开元
赔率60倍
免费呦呦游戏
少女·网红·破处
反差女神外流
萝莉直播大秀
黑丝人妻NTR
免费呦呦破解